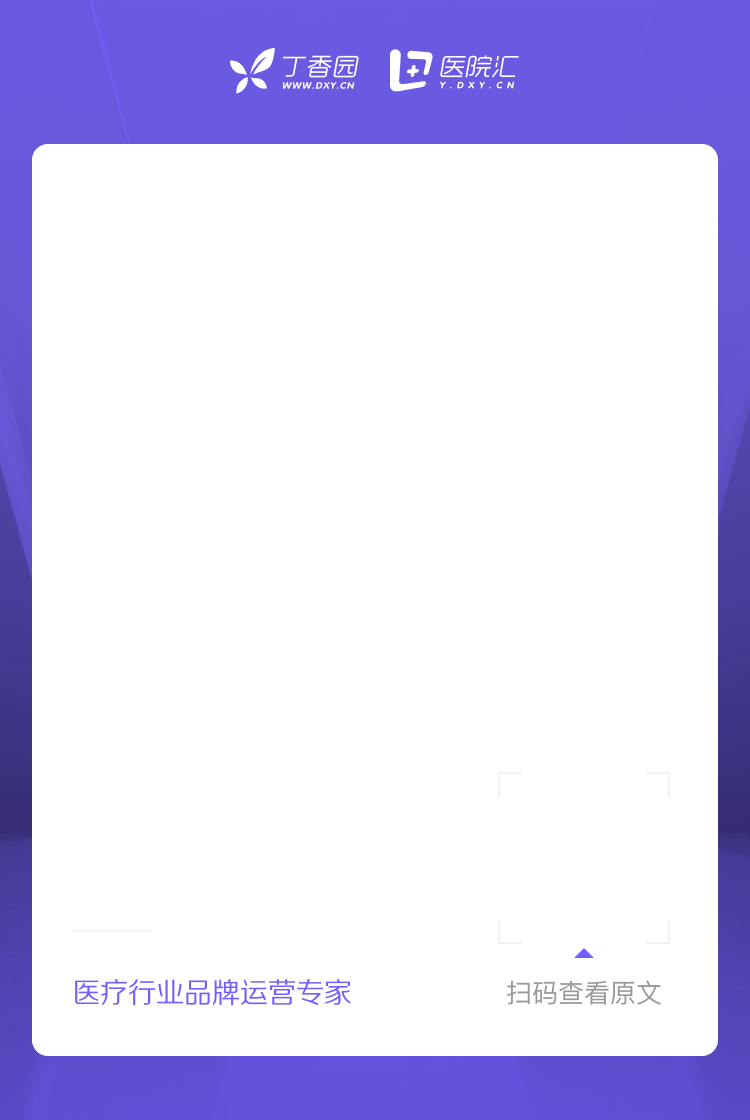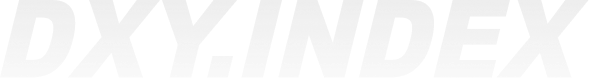每 7 至 8 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人死于癌症。一个典型的 4+2 + 2 的家庭正好 8 口人,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多数人将在人生的某个时间节点,面临一场和癌症的遭...
每 7 至 8 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人死于癌症。一个典型的 4+2 + 2 的家庭正好 8 口人,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多数人将在人生的某个时间节点,面临一场和癌症的遭遇战。
在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可以治疗、控制、甚至治愈的慢性病 10 年之后,癌症一词仍然有毁灭性力量。
一位经历了父亲癌症过世的女儿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我觉得每个家庭都应当准备氰化钾,如果我得了癌症,就立即吃下去,我不能接受自己成为折磨亲人的那个癌症患者。」
问题不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这种永恒的疾病 ,而是我们何时会遇到它。当这场不可避免的遭遇战来临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我们为此探访了多个家庭,癌症外科医生、癌症内科医生 、心理学家,还有姑息治疗专家。
这不是一个个和疾病搏斗之后胜利或失败的故事,而是面对医学巨大的不确定性,病人、家人和医生一起,根据自己的人生哲学、经济状况、疾病进展进行选择的历程,是在选择之后,如何保有平静、尊严和生命价值的故事。
这些故事里,有希望、有恐惧、有悲伤,有泪水,有遗憾,唯独没有失败。
指南与人
尊严死倡导者、中国第一部结直肠癌诊疗规范的牵头人顾晋,决定违背他行医三十年奉为圭臬的各种医学规范和指南,为晚期癌症患者李萧进行一项激进的手术。
李萧不适合手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看。
这是中国最顶尖的结直肠癌外科医生顾晋见过的最大的造口部位复发肿瘤,菜花样的肿瘤覆盖了腹部三分之一的皮肤,肝部有疑似转移。
最开始,顾晋只看了一眼病历和影像资料,就否掉了手术的可能性——高昂的手术费用、没有治愈的希望、随时可能致命的手术并发症。
这也是李萧的妻子跑遍了北京所有的三甲医院后得到的一致回复。
彼时,顾晋还没有见过李萧,两年前的直肠癌手术后,肠道已经无法和肛门相连,于是将肠道的一部分外置于腹部表面,形成一个造口,用护具包裹住,代替原来的肛门功能。最大的区别是,人造的新肛门没有自我控制的能力——这是超过 50% 的低位直肠癌患者不得不面对的窘境。
因为虚弱,更因为难堪,李萧不出门。整个 2016 年的冬天,李萧躺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小旅馆内,等待妻子果果每天带回来的坏消息。
在那些寒冷而漫长的冬日,果果都会带上一沓病历,跳上早班公交车,前往头一天晚上圈定的医院,等上几个小时,看看有没有一位医生愿意接下李萧这个病人。
被无数次拒绝后,果果又会坐上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回到小旅馆,第二天换一家医院,重复同样的过程。就像荷马史诗里的西西弗斯一样,无望却执着地履行自己的责任。
李萧和果果约定,这是最后一次尝试。
果果租了一幅轮椅,把李萧带到了顾晋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他是这家医院的院长)的诊室。顾晋有些发愣,阅读黑白胶片、病理报告上的数字和直接面对一个被消耗的年轻癌症病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冲击。
3 月底的北京,暖气刚刚停止供应,被带进来诊室的,除了门外的冷空气,还有一股隐约的粪便的恶臭。
轮椅上的年轻人脸色惨白,和多数来到这个诊室的客人一样,虽然处于人生最暗无天日的日子,还是试图对对面的医生扯出一个笑容。
当顾晋请李萧躺下做检查时,他往后缩了一下, 讪讪地说,「大夫,有点脏。」
只掀起了衣服一角,恶臭在不大的诊室里弥漫开来。
肿瘤复发在腹部表面的造口处,肉眼清晰可见,菜花样的肿瘤开始溃烂,比起上一次看到的照片和病历,腹壁上的血红色肿块似乎又长大了不少,已经没有任何护具可以遮盖,脓血和粪便从溃烂处往外翻涌。
李萧把头别向一侧,「您看我现在这样,没法出门,我一点尊严都没有啊!」
一端是一个 32 岁的年轻人热切的目光和余生的尊严,一端是汇聚了最可靠的医学证据和顶尖临床医生意见编制而成的指南。
向来果决的顾晋,一时踟蹰不语。
只有上帝知道
医学是一门充满不确定性的科学。
作为顶尖的外科医生,顾晋每天面临大大小小无数个选择:
75 岁的老人同时患有肺气肿、高血压和冠心病,还能不能手术?是扩大手术范围以绝后患,还是尽量保住这个 20 岁年轻姑娘的肛门?来自河北农村的病人家境贫寒,是直接手术,还是先做一轮新辅助放疗?
哪怕已经进入精准医学时代,医生们试图干预疾病的种种努力,并不一定会通向一个确切的好的结果,癌症尤甚。
具体到某个特定的人,这个昂贵的靶向药物一定能奏效吗?手术后肿瘤会不会复发?只有上帝知道。
屡败屡战之后,人类短暂地找到一些对抗癌症的武器:
外科的大范围切除术有可能能降低复发率,但是病人们会失去乳房,肛门、食道等重要器官; 还有一定的几率,生育的能力,性功能会受到不可逆的伤害;在一些脑部、脊椎肿瘤的手术里,病人甚至有瘫痪的可能。
一些化疗药物,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杀死了正常的细胞,带来恶心、过敏、出血等副作用,以及不菲的花费。
而治愈终究是小概率事件。在穷尽现代医学的所有手段之后,在中国,癌症的 5 年生存率也不过 30.9%。
在罹患这种疾病的那一刻起,就失去最优选择(对于多数人而言是治愈)的机会。不过是两相其害取其轻的妥协,是在众多的不确定性中,找到一个相对没那么糟糕的结果。
风险和机会并存,黑暗与希望同在。
如果最优的选项不存在,结果的好与坏很多时候是病人的主观感受,更重要的是,找到一条他觉得有价值的未来的路。
李萧跟顾晋谈及女儿和自己作为父亲的挫败感。女儿半岁时,李萧被查出结肠癌,全家都被拖入癌症的轨道,他和妻子频繁地往返于北京和石家庄的家之间,没有再工作,女儿也托付给老人照料。
肿瘤、脓血、肠造瘘、缠绕着身体的恶臭,让李萧没法出现在有人的地方。他渐渐失去了作为父亲、丈夫、下属、儿子、朋友的全部社会角色。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写道,癌症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疾病,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和政治范畴的疾病,一种充满惩罚意味的疾病。
日常生活被一一被抹杀:没法穿衣,衣服粗糙的纤维会摩擦刺激肿瘤的表面,怕被人嫌弃不敢出门,连一个拥抱也不敢给女儿。
「您不要拒绝我,我们已经走了许多医院,您要不给我做, 我只能等死,不,这样生不如死…….」
顾晋决定给李萧手术,他希望这个年轻的父亲,能有尊严地度过他的人生——无论长短;能在拥抱自己女儿的时候不再感到内疚;能走出寄居的小屋,找回做为父亲、丈夫、儿子的社会身份。
100 万买 10 个月的命,买吗?
在关于癌症治疗的复杂的数据模型里,除了生存期、有效率、治愈率、瘫痪的几率、并发症的可能性这些令人费解的排列组合,还有更为残酷的变量——钱。
艾美仕——一家全球性的医疗信息提供商的数据显示,2015 年,拥有私人保险的癌症患者年平均花费是 5.8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近 40 万元。
在过去的 5 年间,有超过 70 种抗肿瘤的新药上市,可以延长那些原本被认为罹患了最为致命的癌症的患者的生命,比如晚期黑色素瘤和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价格也不菲。2014 年,FDA 批准上市的抗肿瘤药的人均年花费高达 12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 80 万元。
尝试一种昂贵的新药,延长自己或家人几个月到十几个月生命,代价是几十万,你怎么选?
就连医生也没有答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张晓东记得,一个小伙子带着癌症晚期的妈妈四处求医。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还是询问昂贵的靶向治疗。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靶向药并不百分百有效,受益人群在 20% 左右,我要是说可以试试,如果他因为没钱,那么今后心里的遗憾、歉疚将伴随终身。」
最绝望的时候,杨洋想过离婚,卖掉和丈夫共同拥有的房产,将自己的那一半房产用于给父亲治病。
2013 年 7 月,父亲被查出结肠癌肝转移。杨洋和医生商量后,决定采用靶向药西妥昔单抗加化疗药物伊立替康的治疗方案,争取手术的一线希望。
一支 20 ml 的靶向药 4698 元,不入医保。但对于杨洋父亲这样的 K-ras 基因野生型结肠癌晚期转移患者,确有疗效。
德国医学肿瘤学协会的一项临床研究显示,使用这种靶向药加化疗药的结肠癌晚期患者,中位生存时间是 28 个月——一半以上的患者活过了 28 个月,对于晚期病人而言,这算得上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数据。
在开始治疗的前三个月里,杨洋的父亲用掉了 30 万,这也是主治医生此前预估的全部治疗费用。
杨洋是一家杂志社的记者,而丈夫在一家国企工作,家庭月收入 25000,两人赶在北京房价跳涨之前凑齐首付买下了一套新房,月供 3500。饶是如此,面对六七位数的医药费,杨洋仍然觉得天旋地转。
父母已经卖掉了老家的服装店铺,还举债 20 来万。杨洋每晚失眠躺在床上盘算,「100 万难道就只能买我爸 10 个月的命,我去哪儿凑这些钱 ?」
杨洋找附近中介打听,她和丈夫两年前买下的北五环外的一套复式两居,时价 280 万。绝望中,她试探着向丈夫提及离婚 ,「我们把房子卖了,我拿走一半钱,带着爸妈,能治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不拖累你。」
老家的亲戚朋友婉转劝说杨洋和母亲放弃,不要「人财两空」,但最新的 CT 结果显示,靶向药对父亲确实有效,肿瘤已经从十几个减少到 6 个,虽然不能立即手术,但希望似乎就在眼前。
你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面对癌症这道选择题,当医学没有办法给你最优解时,选择哪种方案,是不同的人生哲学之间的较量,关乎你和你的家庭未来想要哪种生活,并无优劣对错之分。
总有一些富有战斗精神的人,不想盯着存活统计数据,想尽力「积极应对」诊断结果,有医院愿意收治,有手术可做,有药可用,也许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还有一些在旁人看来「显然」要放弃的方案,可能对这个人和他的家庭而言,是最好的选择。
张晓东说起她的一个朋友,低度恶性的淋巴瘤,但她不愿意化疗,当然也没有用各种江湖偏方,5 年后去世。
「她不后悔」,作为肿瘤医生,张晓东觉得,这也是很赞的选择。
4 年前,浙医一院的急诊科医生、医学博士陈作兵,在父亲被诊断出恶性腹膜间质瘤晚期后,放弃了化疗放疗,将他送回了浙江诸暨老家。
这是陈作兵父亲自己的选择,陈父喜读《庄子》、《老子》,对生命有自己的见解,他说人好像溪流一样,一开始是一滴滴水,然后是小溪,到了青壮年期声音会越来越响,波澜壮阔,最后无声无息地回归大海。
他选择回到出生的地方,在诸暨的山里种下了南瓜和苋菜;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和亲人朋友告别;和孙辈一起,度过一个极为热闹的除夕夜,拍了许多张全家福。
翌年 3 月,陈作兵的父亲在平静中离世。
陈作兵说,选择是没有对错的,任何一个选择,只要是充分了解病情之后,凭着自己的理性和思考做出的,都是正确的。
做了 20 多年癌症专科医生,张晓东认为,肿瘤治疗有很多时候是站在十字路口,往哪边走都有道理,利弊一样,需要患者和家属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重要的是,不要回头,治疗窗口转瞬即逝,只能一条路走到底,否则对病人和家属都是心理折磨。
医学的美妙之处又在于,总有不确定性存在,那些斗志昂扬的人们,希望采取积极的战斗方式,将生命延续足够长的时间。总有微弱的可能性存在,等到新的更好的疗法问世。
杨洋的母亲用一句话浓缩了丈夫的一生——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住在女儿家治疗的时候,化疗让他有些昏昏沉沉,一日,他趴在洗手台上吐,杨洋下班带回来两张京剧的票,问道「爸,我这里有两张演出的票,你去不去?」
杨父一听,忙不迭地说去,去,去。
母亲回来跟女儿「告状」,演出完了你爸也不肯走,就在乐池附近不停地给人鼓掌,叫好好好。
关于癌症治疗的一个误区是,治疗,尤其是化疗会摧毁病人的身体,不但让人痛苦不堪,还会让病人死得更快。
作为癌症内科医生,张晓东碰到病人和家属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化疗会不会死得更快?」,「化疗副作用那么大,他承受得了吗?」
在张晓东看来,是否具备化疗的可能性,是医生判断的。病人和家人可以根据意愿和经济状况决定是否接受。但由于化疗有效率有限,有一部分患者化疗无效后,肿瘤不受控制地长大,导致症状越来越重,最终导致死亡。家人误认为是化疗所致,其实是疾病进展所致。而化疗有效的患者,生活质量会得到改善。
杨洋的父亲算是幸运,最开始,化疗和靶向治疗副作用也不算大,起了些皮疹,有些恶心,除了化疗那些天比较痛苦,「但过了该吃吃,该玩玩,心里并不存什么事。」
阶段性的治疗结束后,杨洋会带上父亲母亲,去吃一顿海底捞或是韩国烤肉,作为庆祝。
父亲喜欢站在女儿家朝东的窗户下,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见顺义机场飞机的起降。没有坐过飞机的父亲会问女儿很多有关飞机的问题,比如,你说飞机为什么会在天上拉白线呢。
更多的时候,父亲每天去超市溜达一圈,买菜,给女儿女婿做好吃的 ,像所有寻常父亲一样。夏天来了,小区楼下多了个吹笛子的老头,父亲会拉二胡,两人总是在傍晚时分合奏一曲《梁祝》。
6 个月的靶向加化疗的联合治疗为杨洋的父亲博到了一个手术的机会,而手术意味着根治的可能性。
如果还能吃巧克力还能看足球直播,我愿意活下来
选择永无尽头。疾病的过程就是一个个连续选择的过程,刚做完一个选择,下一个选择又接踵而至。
杨洋的父亲就诊于北京肿瘤医院——中国最好的两家肿瘤专科医院之一,院方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正值壮年的主治医生翻来覆去把片子看了一遍又一遍,整个科室的医生开过大会,研究过手术的方案。
杨洋挺着肚子,她当时已经怀孕 30 周,和母亲、姑姑一起站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
手术进行了半个小时,主刀医生发现肝部有一颗 CT 上没有显示的肿瘤,这里是影像学上的盲区也是现代医学的局限性所在,在开腹之前无法探知所有角落。
摆在杨洋面的,又是一道棘手的选择题:肝部的这颗肿瘤位置极差,需要切掉四分之三的肝部,切不切?
「医生,这意味着什么?」
「他可能长期卧床,」
「手术之后还能化疗吗?」
「切掉大部分肝,病人会很虚弱,暂时不能。」
「会复发吗?」
「很可能会。」
「复发怎么办?」
「再切。」
对话进行地飞快,决定要在须臾之间做出。
作为女儿,杨洋明白父亲想要活下去的意愿有多强烈,但也明白父亲的底线在哪里。
手术前,杨洋和父亲有过一次半正式的谈话,谈起父亲的一个病友的造瘘手术,在腹部再造一个人造肛门, 用袋子兜住排泄物,定期更换。父亲当时很坚决地说,他绝对不能接受,如果让他挂上那样一个袋子,他宁可去死。
杨洋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不切了。」
主刀医生说好,那肝就不做了,只把结肠上的肿瘤切掉。
「如果无法选择积极治疗时,确定病人所能接受的底线,确定病人不想要什么,更为重要,」刘巍说。
刘巍是北京肿瘤医院姑息治疗中心的主任,每次给出自己的意见前,刘巍总是会问:您最害怕什么?您希望治疗给您什么效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您愿意承受什么?不能放弃什么?如果您的愿望,我们暂时还不能做到,有没有次优的选择?
哈佛医学院的的教授阿图 • 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中》写到,有时候我们可以提供疗愈,有时候只能提供慰籍。但是无论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我们的干预,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和牺牲,只有在满足病人个人生活的更大目标是,才具有合理性。
阿图的同事苏珊 • 布洛克,哈佛医学院的姑息护理专家,在父亲脊髓肿瘤手术前,跟他进行了这样一次谈话——为了博取一个活命的机会,你愿意承受什么?
这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荣誉教授的回答让女儿大吃一惊,「如果我能够吃巧克力冰激凌、看足球直播,那我就愿意活着。如果能有这样的机会,我愿意吃很多苦。」
这个谈话至关重要,因为术后,他的脊髓出血,危在旦夕,摆在女儿面前的有两个选择:就此放手,让父亲离去;再进行一次手术,但他可能会永久残废。
苏珊问主刀医生,如果父亲活下来,是否还能吃巧克力冰激淋,看足球直播。得到肯定答复后,苏珊请主刀医生再进行一次手术,「感谢那次谈话,我不需要做什么选择,他已经做了决定。
手术后,苏珊的父亲又活了十年,虽然需要有人帮忙洗浴和穿衣,但还能步行一小段距离,完成了两本书和十几篇学术论文。
医学治病,也治人
以姑息医学的兴起为标志,以疾病为中心的现代医学实践开始关注人的需求。
作为一门关注症状缓解和生活质量的医学分支,姑息治疗并不以治愈疾病为价值导向,而是关注病人在疾病中的种种生理和心理感受。
从门诊大厅坐电梯上四楼 ,穿过长长的走廊,走下 10 级台阶,左手边一排房间是刘巍所在姑息治疗中心。
穿过医院里熙熙攘攘的人流,最终来到姑息治疗中心的人不算多。刘巍每天上午的门诊大概看 10 个病人,她的门诊时间通常很长,因为她需要给每个人预留不少于半个小时的时间。
先是听,有时候病人或是家属会陷入失败的治疗的讲述中,宣泄情绪的时候更多一些,但刘巍很少去打断。
一位年届中年的女儿描述起患病的母亲心重,怕花钱,怕拖累子女,刘巍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回应,「我猜您妈妈一定爱你们,代我向她问好。
「他们有痛苦,倾诉也是一种治疗。」
门诊结束后,刘巍的学生薛璐叫住病人或者家属,递上一张名片,上面留有诊室的电话和微信服务号,「不是 24 小时都能找到人,但工作的 8 小时可以。」
在刘巍看来,姑息治疗是对癌症整体进程的积极干预,是涉及领域众多、体系庞大的一整套治疗体系:对疲乏、疼痛等躯体症状的支持;对恐惧、焦虑、失眠等情绪的照拂;对病人的生活、社会角色剧变的干预。「让患者能够安详、平静而有尊严地离世,甚至包括居丧期服务。」
姑息治疗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作为一种理念——关注病人本身的理念贯穿整个癌症进程的始终。
唐丽丽会鼓励病人花更多的时间家人呆在一起,而不要奔波在医院和家的途中,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家人做一顿饭,出去看一次音乐会。
如果疼痛,也不要忍着,寻求医生的帮助,「当生命品质发生无可逆转的退化时,这个社会仍然能够给予临终者免于痛苦和恐惧的可能性,临终关怀是一个文明社会所能给他的成员提供的最好的保障。」
杨洋选择和母亲一起和父亲进行这场艰难的谈话。
父亲在知道病情之后问了一句「那我最后什么样?」还没等女儿没回答,自己又接了一句,「肝硬化」。
这句话让杨洋难过了许久。
杨洋说,爸,如果你真的想做介入治疗,我来出这个钱。但你还有一个选择, 把这笔钱拿出来,我们一家仨出去玩一趟。我怕你做介入之后,我们没机会了。
虽然不断升高的肿瘤标志物提示了癌症的恶化速度,但父亲的身体素质仍然不错,一家人决定去云南,24 年前,杨洋 9 岁的时候,和父母一起去过一趟云南。
24 年后,父亲仍然把自己当成家里的主心骨, 到大理后,父亲开着租好的车,沿着洱海公路一路开向双廊古镇。
杨洋记得那天天还没亮,天上的星星在闪呀闪,路不怎么好,但父亲的车仍然开得很稳。在古城的夜晚,父亲指着猎户座中部的三颗亮星说,他一直认为那是一家三口人。
这是成年之后杨洋和父母第一次出行,也是最后一次。回家后不久,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再也出不了远门。
最后的最后,杨洋没有进行任何的有创抢救,连输液都撤了。最后一次醒来的时候,父亲跟女儿说, 他并不害怕,也没有遗憾,他的非洲鼓二胡音响都不需要带,打墓的时候把底下打得平整些 。
从查出癌症到过世,一共 2 年零 10 个月,治疗支出 100 万,杨洋感谢父亲的坚持,等到了外孙女欢喜的出世,「他抱过欢喜,欢喜记得姥爷。」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更多医学人文精彩文章,前往医学时App查看>>http://dxy.me/z2EBny。
好文章,需要你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