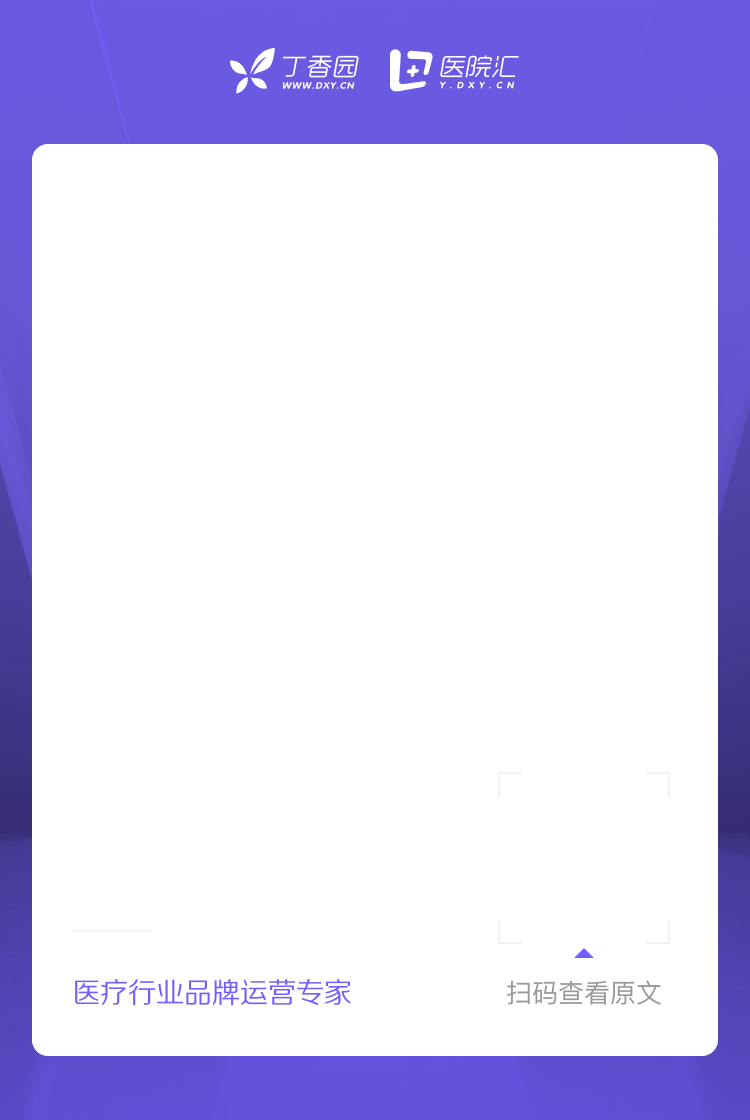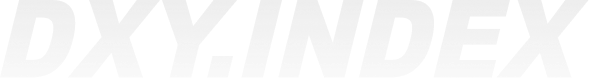面对医疗这件事,地域与出身,其实并不重要,靠谱才是硬道理。
医院,好像围城。
围城里,是时不常受到开放政策撩拨,想出去试水的一大拨医生。围城外,是孜孜不倦尝试走进来的另一大拨医生,他们可能因为出身、学历、地域、语言等各种原因,被关在外面。
下面,是 3 个分别来自港、台、日的女性,心甘情愿走进围城,当起北漂的故事。

被无差别对待的住院医
台湾人来大陆学医或当医生,其实隐隐存在着几种主流套路:
如果是学医,由于台湾目前尚未认可大陆的学历,通常之后是男生回台服兵役,然后再去美国或欧洲考医师执照。
如果是当医生,从专科类型上,大家会更青睐于医美、皮肤等领域;从地理位置上,大家会更喜欢福建、广东等靠近台湾、台商较多、经济较发达的省份;从机构上,大家或者选择厦门长庚医院、南京明基医院、东莞台心医院等与台湾有关系的医院,或者选择高端私立诊所;在执业时限上,遵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司在 2009 年出台的管理规定,大家通常也以 3 年的短期执业为限,有的在大陆工作一段时间就离开,有的则是短期外派到大陆,有的是利用假日来当医生。
而来自台中的「80 后」潘中婷,却不属于上述情况的任何一种:
当时不到 20 岁的她离开家,独自来到北京;先用 5 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读了临床医学本科;再用 5 年,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修完硕士和博士;然后正式进入北京某大型三级医院的眼科,现在已工作 4 年多,是正儿八经的一位主治医师了。
她现在已经跟大陆绝大多数同龄的医生,过着并无分别的日子了:
成为科里干活的主力,每周出 2 个半天的门诊、管床、上手术,1 个月的出院患者能有 40 多人;
为晋升副主任医师准备发论文、攒轮转年数、计算诊疗量和手术量;
在这个互联网热的时代,定期给患者写一写科普文,交给科室转发给各大媒体,或做成海报贴在院内,有的节假日还要去周边社区或外地做义诊;
微信朋友圈里转发医院和科室的最新消息;
甚至,她还很「接地气」地 3 次收到过患者送的锦旗,1 首患者作的诗,和复诊患者给她带来的自家种出的杏。

不走寻常路的潘中婷,其实当年选择到大陆念书,经过了仔细的考量和比较。这背后影响作用最大的,是她的医生爸爸。潘爸爸原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内科医生,后来台湾也经历了类似于今天大陆的医疗开放过程,就自己出来办诊所,经营至今。
「爸爸更看好大陆的前景。」潘中婷说,小的时候,爸爸就经常鼓励她和弟弟未来学医,所以最初时,她在台湾的一所大学读药学专业。对大陆动心,源于潘爸爸朋友的孩子暑期分享自己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求学的经历,潘中婷也想试试,「不过后来爸爸朋友的孩子又跑到波兰读医学院,反而是我一直留在大陆了。」
「最初投考大陆医学院的时候,其实还抱着一种希望,就是未来台湾能承认大陆的文凭,但到现在也还没有。」潘中婷回忆,「后来一直在大陆念书,慢慢就会觉得,能遇到这么多患者,见到这么多病例,学到东西这么多经验,如果能留下工作的话,就会更好。」
其实,她最初找工作的时候,也考虑过湖南和江苏的两家台资医院。然而比较来比较去,潘中婷又舍不得自己已经生活了 10 多年的北京,「却望并州是故乡」,到底还是留在北京了。
现在,潘中婷与自己台湾的高中同学聚会时,大家都会很羡慕她能在经济发展更快的大陆工作,希望自己也能被外派到大陆上班。不过,跟留在台湾做医美的同年资医生相比,潘中婷的收入还是略少。对此,她倒不以为意,「我从一开始就更喜欢以治疗为主的专科。而且看爸爸的经历和经验,都是在医疗市场放开后会有更好的前景,我也相信大陆未来的发展只会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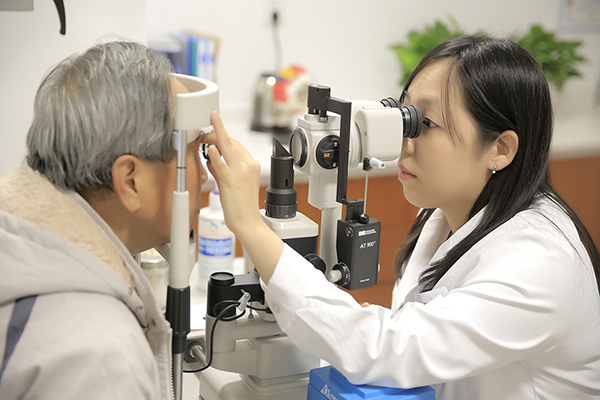
目前她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业务。「一方面,在患者服务和交流上,我总喜欢多说几句,让他们对疾病更了解。」比如虹膜睫状体炎比较严重的患者,就不能完全按药品说明书上的用量,一天只点两次药。潘中婷就会拉着患者,再多嘱咐几句,并在他的药方上再写一遍推荐的用量。
而很多患者一听她讲话的腔调,就好奇她是哪里人,在得知她来自台湾,更是忍不住多问几句。「我没感到过被冒犯,或被隔离在外,」潘中婷反而觉得,「台湾人」的标签,倒是让患者和同事对她多了份友善和照顾。

另一方面,她也逐渐开始考虑自己的亚专科发展方向。「我相信现在是屈光的时代,我也希望患者在各种环境下都能很舒服地看这个世界。」潘中婷想选择近视眼手术的方向。
工作以来,她的科室做了 400 多例近视眼手术。潘中婷是个有心人,她会比较哪一台机器测角膜厚度更精准,还收集并梳理了患者的资料,根据不同度数的患者,观察术后效果,从而反向追踪考量术前的手术方案设计。
潘中婷读书时就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如今在北京安家立业。她引用自己另一位台湾同事的话,「我们只是来自不同的地方。」
两次转型的医务社工
改变方向这种事,其实有些痛苦,因为背后隐含着对自己过去的批判,和对自己未来的打碎重塑。而这种痛苦,「90 后」的杜今经历了两次。
杜今看起来文弱温柔,而谈吐又有着一种不像「90 后」的职业、坦率和灵巧。

她家在河南安阳,本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读社会工作专业,比较偏青少年方向,毕业后又申请到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内地同来的同学,有南开的、人大的,还有北大的,2 年读书,1 年实习,毕业后可以拿到香港注册社工。作为独生女的杜今,一帆风顺。
第一次改变方向,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本来,杜今的学术研究和实习都是青少年方向,而一进入实习阶段,她发现,面对开朗活泼的孩子,首先自己的精力和体能就很难支撑满一天,而且相对沉稳的性格与孩子也不是很合拍。坚持做了小半年,最终杜今还是觉得自己不适合。
她向导师求助。导师推荐她尝试一下医务方向,到香港大学玛丽医院肿瘤科做实习。「我当时特别担心,奶奶因肺癌去世还没多久,我怕触景生情,怕接触的都是消极负面的环境。」杜今很忐忑。
然而,她在肿瘤科实习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越做越开心。
在香港,如果是肿瘤的新症患者,不论是看门诊,还是接受住院治疗,都会收到资料袋,其中就有关于院内社工资源的介绍。如果患者感兴趣,就会先填写个人资料转介同意书。医生进而把这些患者对接给社工,未来还会告知社工这些患者的病情转变。
而具体到杜今实习的癌症病人关顾支援组,3 名工作人员都是注册社工,每个月都会组织包括静观减压、舞动治疗等在内的专业心理支援服务,以及包括书画、太极、出游等在内的兴趣小组,这些活动均会标注适合的参与对象,例如新症患者、康复患者等类别,然后寄送到患者留下的地址。患者接到信后,自愿报名参加。
「香港患者的接受度很高,他们很愿意走出来寻求帮助,有这种社会氛围。」杜今在实习期间开展了 2 个支持性社工小组,利用舞动、音乐、绘画等表达性治疗元素,陪伴并协助一些看似坚强乐观的肿瘤患者,逐渐寻找身边的支持系统,例如病友、家人、朋友等,并学会表达自己的压力和恐惧,学会分担别人的消极和崩溃,「我认为,社工其实起到的是辅助作用,最重要的是,患者自己找到了调整的方法。」
杜今在实习过程中,迎来了很多新症患者,也运用舒缓疗法送走了一些患者。她选定了医务社工这条路,也波澜不惊地渡过了第一次改变。
找工作的时候,杜今的同学,大多选择留港或是出国,还有个别同学选择回内地,他们大多去了大型基金会或者社会福利类相关的企事业单位。
「我还是想当社工。」杜今知道一线社工的待遇和地位相对差些,「但我更享受在一线与人打交道,不太想坐办公室,所以压根就没考虑过别的,就是要找一线社工的工作。」
她也选择回内地,一是想离家近点儿,二是因为香港社工的资源其实很饱和:社区、医院、老年公寓里的社工都非常充足。「如果留在香港,我只是那么多社工中的一份子;如果回内地,在社工起步期,我多多少少能发挥更大作用。」
虽然下了决心,为求稳妥,杜今还是专门在暑假到北京找已经在医院做社工的师姐,进一步打探了大陆的医务社工发展情况后,才最终做出决定。去年 5 月,她进入北京一家新运行不久的大型三级医院,归属门诊部,做唯一一名医务社工。
然而,即使提前有了心理准备,了解了大陆情况,杜今没想到,第二次转变方向正等着她。而且,这次远没有第一次容易。
「记得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老回家跟我妈哭,」杜今再说起来不太好意思了,「我那会儿觉得落差一下特别明显。从社会,到患者,包括医生和护士,感觉大家对我这个专业和岗位的认可度,跟自己设想中的都有差距。每天的工作内容,跟自己以前的所学所做也有差距,所以就有点受不了。」
杜今知道不能一下照搬香港的经验到大陆,也知道香港的经验不一定就适用于大陆,但,真的面对时,现实显然以更直白的方式打击了她。
所幸,她没有一直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怨自艾,而是走出来,试着跟大家多沟通,有自己的学姐和以前的老师,也有现在医院的同事和领导,慢慢她聊出了医院的需求点,也聊出了自己的切入点。
现在,杜今形容自己当时的设想,用的词是「飘着」,「一开始,我想的都是专业服务,没有落地,后来,我尝试着去看看这个医院,在部门领导的指引下就慢慢地从志愿者这里,跟门诊服务流程挂上钩了。」

杜今现在带着 1 个北京城市学院派来的实习生,管理着约 200 人的活跃志愿者,包括培训、指导上岗、考核、评估、定期活动等一系列内容,其中门诊志愿者提供指路、自助机使用、解答问题、特殊患者就诊陪伴、协助医院举办义诊或健康月的活动、音乐演奏等形形色色的服务,还担负起医院门诊和护理部的患者满意度调研。
而在她一开始特别看重的专业服务方面,也有了尝试,比如在儿童血液病房做了分别面向患儿和家长的活动,比如在病房利用推车做移动图书馆和床边伴读。未来,她还要打算跟一些社工事务所或基金会合作,共享一些资源和专业服务。
换了一种角度,就海阔天空了。
「以前我总想的是,自己的专业如何能不断往前走,现在在医院待久了,特别喜欢医院的氛围,想的是怎么能把自己的专业和医疗领域结合好。」杜今终于心甘情愿地完成了第二次方向转变,现在,她期待更多同路人,自下而上地推动起医务社工这个领域的发展。
享受新鲜的日本教授
当然,这个「新鲜」并不是指北京的空气。
瘦小精干的藤泽茂子,在康复界是个名人,临床和教学经验都很丰富,而且跟中国渊源长久。她不但是日本最早期的物理治疗奠基人之一,还很早就参与到为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培训人才的工作里。
某一天,当她还在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学物理治疗系做主任的时候,听校方说,有个到中国工作的机会,她非常高兴,「我特别喜欢挑战一些没经历过的新鲜事。」
藤泽茂子从年轻时就喜欢挑战新鲜事物:当日本刚建立康复学校的时候,她就特别有兴趣,终于考取成为第三期康复治疗师;当很早就在综合医院里建立康复科的庆应义塾大学医院刚建科的时候,她又是最早一批去工作的,一干就是 25 年。
这次来到北京,她要面对的新鲜挑战是,如何在异国他乡,把一个刚起步的康复医院的核心单元——康复治疗部里的人员培训带教好。
藤泽教授不是来挂个名的教授,也不是来坐办公室的教授。她喜欢用 PPT 讲解一些康复的技术和手法,更喜欢在康复大厅的现场「溜达」。在一趟一趟来来回回的走动里,不论是患者、家属,还是医务工作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沟通。
「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只会一些简单的对话,主要还需要翻译。」藤泽教授说,「我特别喜欢,也特别享受这样的工作状态,能为大家解决一些小问题尽一些绵薄之力。」

多年与中国康复医生打交道,藤泽教授其实比较认可中国医生的康复理念,认为西方一些先进的理念已影响到中国,因此,她在指导工作中,更强调安全与风险意识的培养和管理,以及职业礼仪的建立,包括如何谦逊地与患者和家属沟通,如何获取尊重和信任。
由于康复医院里还有重症监护室(ICU),藤泽教授更是要求,从 ICU 里就开始做床旁康复治疗训练,以防止关节挛缩或变形、肌肉萎缩、深静脉血栓等影响预后的事。「那些病情较重、住 ICU 时间较长的患者,可能出现很多功能障碍,而这些都不是疾病本身导致的,ICU 里的康复能起到关键作用。」

正因为身处一线,藤泽教授也发现了一些「中国特色」。
首先,是疾病的多样性和病程的多样性,让她很意外。「以前在日本,我从没在一间医院里碰到这么多的疾病种类,而且既有急性期,也有康复期,还有发病后在家住了七八年又来康复的慢性期。」
其次,是中国亲属间的社会习惯。
「日本有患者住院的话,都是自己一个人,家属只在规定的时间里来陪伴一下,最多个把小时,属于探视。也不会出现丈夫生病,妻子辞职来伺候的事情。而中国属于陪护,一人生病,即使请了护工,亲朋好友也要轮流来看护。」藤泽教授笑着说,「我真是第一次切身感受到这种不同的人情世故。谈不上哪种更优越或更科学,只是觉得,很有意思。」
也许,今天你还在留意同事是哪个地方的人,明天你就发现,同事里已经有了机器人。面对医疗这件事,地域与出身,其实并不重要,靠谱才是硬道理。
北大医疗对此文亦有贡献
好文章,需要你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