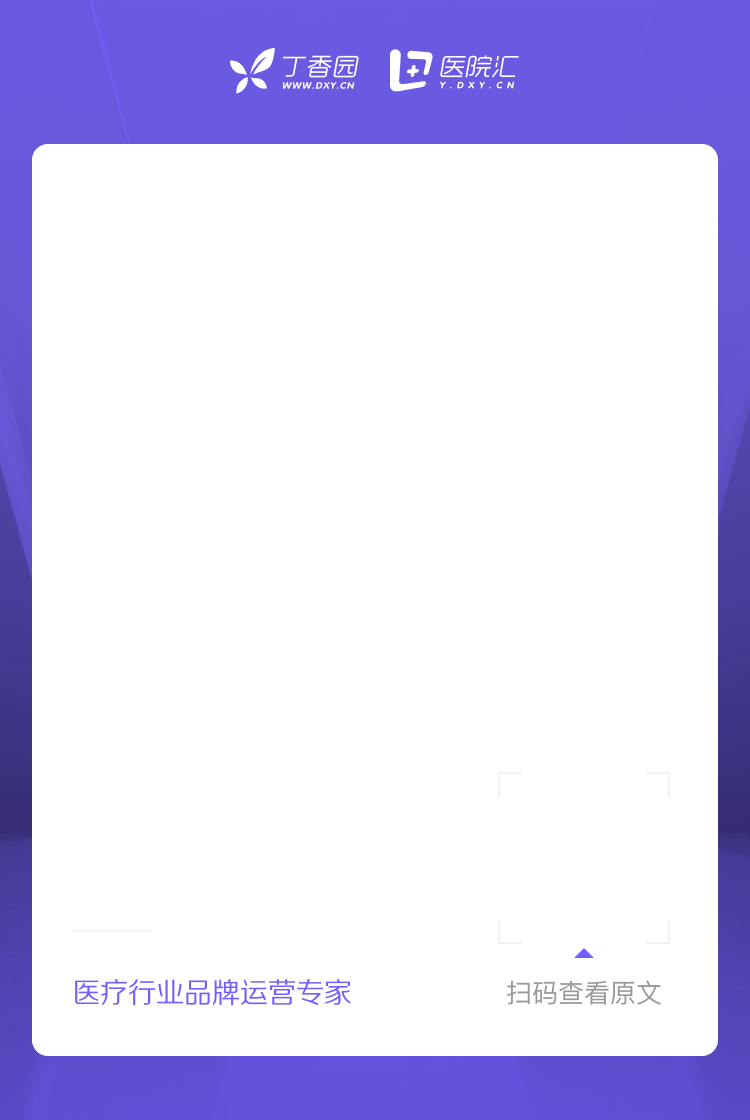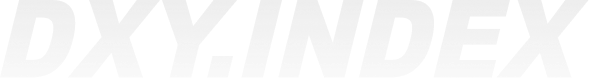过完年,女儿小雨就四岁了。我早早打算好,大年初一就教她学说新昌话「稻桶岁」(四岁),却没想到只提前说了一句「再见」。大年三十,是我调入感染科的第一天。二十九...
过完年,女儿小雨就四岁了。我早早打算好,大年初一就教她学说新昌话「稻桶岁」(四岁),却没想到只提前说了一句「再见」。
大年三十,是我调入感染科的第一天。二十九的晚上,医务科打来电话,说目前感染科人员紧缺,而我有五年的感染科工作经历,此时是否愿意支援感染科。我当即答应,然后就和第一批调入感染科的六位同事一起,赶到医院连夜接受了防控培训。
当时没有人知道新冠病毒究竟如何传播、疫情会如何发展,确诊病例的出现又让局势更为风声鹤唳。进出感染科,意味着存在被传染的风险,我当即和家人商议,决定独居出去。那晚回到家,我特意和女儿说了再见,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了我的抗疫生活。
我们第一批调入的医生主要承担发热门诊的工作,根据医务科排班,我们迅速进入角色,开始了八小时一班的门诊。一身防护的行头,穿脱就会花去不少的时间,而因为戴着护目镜,视野渐渐的就会变得模糊;因为不方便调整口罩绳,耳朵被勒得长出了水泡;因为防护装备宝贵,我们尽量八小时不更换,于是不吃、不喝、不上厕所。
尽管不容易,但大家都下定决心要站好这班岗,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我们知道更辛苦、更危险的是隔离病房里的兄弟姐妹们,生怕自己的退却会加重他人的负担。瘦小的夏芳,那天吃坏了肚子,上吐下泻,但只休息了一天就继续上岗;大个子章勇,口罩戴上八小时,脸上的勒痕要等好几个小时才渐渐淡去;冠玉一戴眼罩就头疼,后来改成了面屏才有所改善;中平老师上完一个后夜班后,睡了几个小时,又赶来上帮班;钰洁临近中午却面对接踵而至的病人,于是午饭也没吃,一直捱到了下班;雯雯姐则和我一样,主动与家人分开住,只能天天在手机里相见。
但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更在乎的是如何诊断治疗好每一名患者,更不漏过一例可疑。一开始不熟悉发热门诊的流程和规范,我们就反复地学认真地执行;不断完善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我们不断地学习;新增的疫区需要注意,我们及时增加到问诊里。那段时间,发热门诊外总有下不完的雨,门诊里头只有劈啪作响的打字声和消毒液挥发后的气息。
发热门诊的夜班是最难熬的,尤其是后夜班。病人不多,但困意、饥饿、寒冷却如影随形。但我们不能脱下衣服去休息,因为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来就诊。有位近一月前曾和疫区返乡人员接触过的阿姨,凌晨 3 点走进了门诊。我反复问清楚情况,又给她做了必要的检查,没有发现被传染的依据,便告诉她不要紧张,潜伏期已过,但建议继续在家隔离,如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情况及时到医院复诊。她离开之后,一直到 8 点下班都再没有人来,而我也数着电脑屏幕右下角的一分一秒,迎来了黎明。
下班回到房间的时候,我会和小雨开视频聊天。我在这边抛橘子、做鬼脸逗她开心,她在那头拼拼图、背唐诗逗我傻笑。长大了一岁的她,我还没好好地牵着她的手去走一走;又长了一岁的我,仿佛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却终究还没能和她坐在一起,翻看她喜爱的《鼠小弟》。
我时常期盼着那一天,我们不用隔着屏幕说再见,不用期待第二天,而是可以一起背《悯农》、背《春晓》、背骆宾王的《咏鹅》。等那一天,我会告诉你:什么是稻桶岁,什么是逆风而行,什么是春暖花开!
我相信,那一天,不远了。
好文章,需要你的鼓励